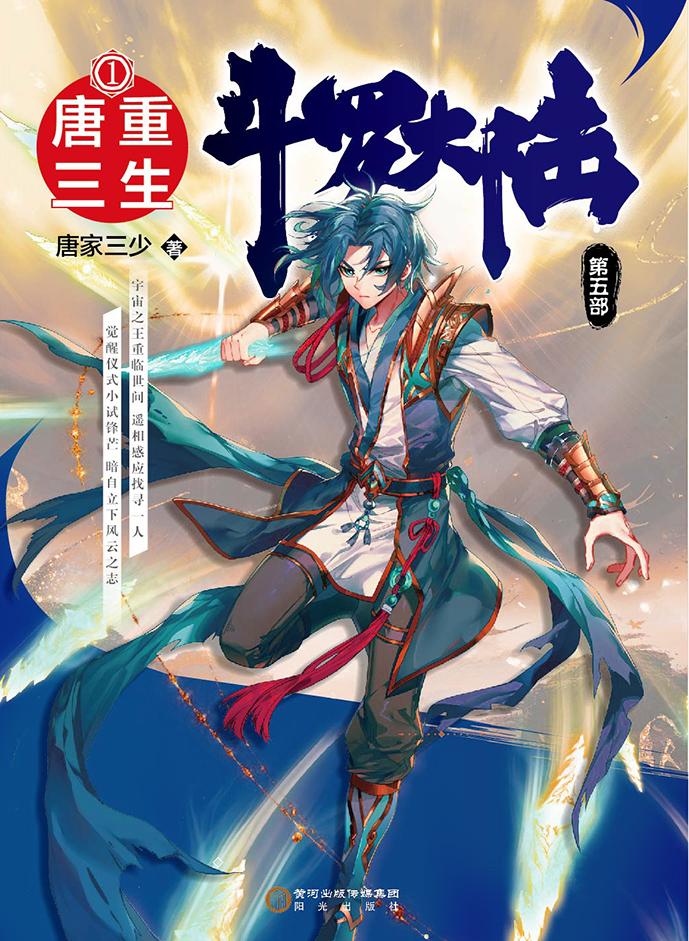耗子小说网>穿成农女,我靠晒霉货成首富 > 第139章 秀女赴宴礼服惊艳引关注(第2页)
第139章 秀女赴宴礼服惊艳引关注(第2页)
“要亮亮的,像太阳照在水面上那样。”她用手比划,“姐你给我做不?”
“等你再长高一点。”我说,“现在布料不够。”
她立刻站首,踮脚:“你看,我己经够高了!”
我笑着捏她脸:“还差三寸。”
她不满意地哼了一声,跑去井边照影子。
晌午前后,王婶来了。她手里攥着块布头,进门就嚷:“哎哟我的穗穗啊,你快看看这个!”
我接过布头,是普通素绢,可边上有一道金橙色的渐变,分明是晒技的手法。
“哪来的?”我问。
“县里传出来的!”她一屁股坐下,喘着气,“说是程家姑娘穿了件奇服赴宴,满堂人都盯着看。皇商当场问是哪家做的,那姑娘张口就说——‘林穗穗货栈’!”
我手一顿。
“真的?”苗苗从里屋跑出来,扒着桌沿踮脚看。
“千真万确!”王婶拍腿,“听说那衣服一站起来,就跟烧着了一样,不是火,是光!皇商连问三遍出处,程姑娘一句没含糊,全说了!”
我低头看着那块布头,手指边缘。这颜色我没教过她,是她自己试出来的。
“后来呢?”我问。
“后来?后来还能怎样!”王婶声音更高,“宴没散,就有小厮骑马往咱们镇上奔。估计是去打听货栈在哪。我说穗穗啊,你这回可真是——”她想找个词,憋了半天,“要出头了!”
苗苗跳起来转圈:“我要穿亮亮的衣服!我要穿亮亮的衣服!”
我坐着没动,心口那块地方慢慢热起来。
原来真的能走出去。
不是靠关系,不是靠运气,就是一块布,一双手,七天的日头。
下午裴煦回来了。他没进院子,站在篱笆外招手。我走出去,他递来一张纸条,折得整整齐齐。
“路上碰见个跑腿的,说是有人托他带给你的。”他声音很平,“我没拆。”
我接过,纸条上一行字:明日巳时,登门拜访。落款是个“商”字。
我翻过来,背面还有一行小字:听闻贵栈有化凡为奇之术,特来求证。
裴煦看着我:“是冲着礼服来的?”
我点头。
“紧张?”
“有一点。”我说,“更多的是……想让他们看看,我们也能做出叫人眼前一亮的东西。”
他嘴角动了动,没笑出来,但眼神松了些。“需要我陪你见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