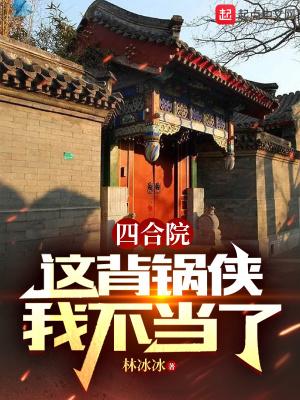耗子小说网>曲终人散花自憔! > 赐锦(第9页)
赐锦(第9页)
原来如此。
哪来无故的偏爱和垂青?不过是早早布下的的棋。
皇帝提拔我,为的是辅佐他心中的储君。
而那个人,不是穆冠雪。
长廊外下起了细细密密的秋雨,身旁的嬷嬷见我魂不守舍,只得紧紧搀扶着,不敢多问半句。我支撑着走过了拐角,忽然之间如裂帛一般痛哭出声,嬷嬷忙含着泪掩我的口,「小姐!小姐!老奴知道小姐委屈,可再委屈也得回家了不是?万万不可在宫里落人口实啊!」
回到了府上,我看见穆冠雪,正和父亲赏字画。
他见到我,瞳仁倏然一亮,「阿樱!」
父亲也含笑招呼我,「樱儿,七殿下有心,特求了冯尚书的画,你不是一直很喜欢么?」
大概是路上哭的麻木,此刻我的脸上一丝一毫的表情也无。
「多谢七殿下,只是,自此往后——」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幽邃深井,字字冰凉入骨,「不必来往了。」
「送客。」
10
那些日子,说长也不过个把月的功夫。
父亲抚摸着凤锦,即便我什么都不说,大概他也猜到了。
然而猜到了又能如何?他唯有在我床前不断叹气,一面念叨着娘的名字,一面怪自己对我管束不严,以至放浪形骸到了今日,锋芒毕露、终于吃了报应。
我将书信一封一封地烧掉,大抵一同烧掉的,还有曾经的吕樱和穆冠雪。
来年开春,吕家家主过世。
射柳宴上,我一身白衣素缟躲在臣子之后,悄无声地遥遥看着。
我看到冯漪珠走向穆冠雪。
他已不是策马兰台的少年,眉宇间隐隐有了运筹帷幄之相,而身旁的少女实在鲜艳美丽,即便只穿一身鹅黄罗裙,全无坠饰,也令其余官女全失了颜色。
「那位是什么人?」我听见人群中有人问。
「冯尚书千金——冯漪珠。」
穆冠雪纵然看上去有些无奈,却并未推开,最终还是答应了教她射箭。
皇帝召见我,颇有些怜悯的意味,大概想看到我失去至亲又失所爱的迷茫痛苦吧?
但我只是深深垂首下去,「臣女服丧,论例守孝三年。若陛下垂怜,请准允臣参加春闱。毕竟后宫不得干政,若臣当真要辅佐弈王,不受非议,这便是最好的法子。」
……
桌上的玉冠雕刻着双鱼纹样,细腻而触之温凉。
我用了整整三年,送走了皇帝,制造党争,伪诏嫁祸,将穆冠雪扶上了皇位,却又不遗余力打压他的亲臣,没有人会怀疑我,也许在文武百官眼中,我便是狠戾毒辣、不择手段的权臣。
包括穆冠雪。
他再不愿正眼看我,即便偶尔对视也尽是冷漠戒备,他只称我「吕相傅」。
镜中人面无表情,可是若细看,眼底沉沉尽是萧索。
我有条不紊地穿好官服,薄抿了胭脂,给面上添三分血色。
门客匆匆来报,说求情的折子终于联名递了上去,到底冯行止是一代鸿儒,以私通之罪下狱太过离奇,甚至传出去民声如沸,纷纷为其求情。
冯漪珠就在旁侧,有些不可置信,「朝中的事,我在后宫尚且不知,民间又是如何知道的?」
我比了噤声的手势,门客只得不语,行礼退下。
「是你?」冯漪珠问道: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,很像是你的作风。吕樱,当年你请旨入仕,是不是因为你心中并不想嫁给穆玄弈?」
我扶正玉冠,微微一笑,「贵妃娘娘追问这个干什么?」
她看着我,迟疑了片刻,「因为……我总想知道……冠雪曾经奉若神明的女子,不是恶人。」
我只是停滞了片刻,便由下人披好了外氅往院中走去,冯漪珠还依依不饶地叫道,「吕樱,吕大人,你回答我!」